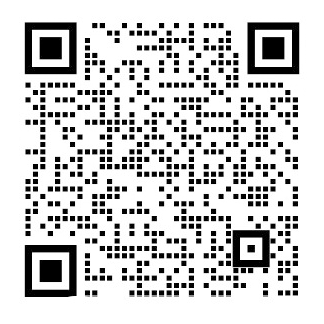Identifying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FDI: The case of Estonia.1
Evis Sinani* and Klaus Meyer**
April 2002
First Draft: December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s widely seen as generating technology spillovers to indigenous firm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Prior research has measured only the net effect of spillovers from FDI on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This paper disentangl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that of competition. We use a production function framework to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rom FDI on the output growth of domestic firms in Estonia for the period 1995-1999. Employing panel data techniques we control for industry and firm specific effects, and a Heckman two-stage procedure is performed to control for sample self- selection bias.
The size of the spillovers var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the incoming FDI and the recipient local firm. The magnitude of the spillover depends on the measure of foreign presence employed as proxy, and it is moderated by the recipient firmrsquo;s size,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trade orientation.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benefit from competition of foreign firms as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induces domestic firms to use more efficiently their existing technologies, or search for new one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maintain their market shares. However, negative side- effects of FDI arise with their headhunting of qualified employees. Thus we find that local firms with high skilled labour experience higher growth, but this growth is negatively affected by FDI in the industry.
Our results, moreover, contribute to the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literature by showing interesting different impact on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 We find that state owned and outsider owned firms benefit from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whereas insider owned firms experience strong negative spillovers.
Keywords: Spillovers, Technology Transfer, Panel Data JEL classification numbers: C23, D24, L11, L60, P31 (spellcheck: US English)
Acknowledgements: We thank Niels Mygind for permission to use his Estonian enterprise dataset. For very helpful comments we thank Jozef Konings and seminar participants at LICO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and participants at Druid Academy Winter Conference 2002.
1 *,**Centre for East European Studie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Email addresses: es.cees@cbs.dk, km.cees@cbs.dk.
INTRODUCTION
The expected spillovers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ve motivated governments in many transition economies to adopt policies aimed at attracting investors. These countries have to modernize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acquire new capabilities to flourish the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restructuring of enterprises is thus a core element of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a central issue in economic research o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nes et al. 1998, Estrin and Rosevear 1998, Buck et al. 1998). It is widely recognized that FDI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the former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 by providing a vital source of investment for overcoming the situation of a collapsing state sector and a slowly growing private sector, and by contributing managerial skills, new technology, capital and competition (IMF et al. 1991, EBRD 1994, Meyer 2001). These contributions are expected to benefit not only the foreign-owned business, but also domestic firms that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owned entity.
Domestic firms are expected to benefit by backward or forward linkages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s and by acquiring modern technology from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as foreign invest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However, there may also b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for domestic firms, such as by loosing skilled employees to MNCs affiliate or increased competition in the host country. A common belief i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s in most cases outweigh the negative ones (UN 2001).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show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f FDI on the local industry to provide a basis to assess policy measures. So far, results have been mixed for both developing (e.g. Haddad and Harrison 1993, Aitken and Harrison 1999)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e.g. Djankov and Hoeckman 1998, Konings 2001). Yet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under which conditions such externalities occur. In this study, we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the siz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productivity of local firms, and on the industry conditions that favor such spillovers.
We focus on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affecting output growth of local firms in the same industry. Our prime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re these spillovers positive, and of what magnitude? How do they vary with domestic firm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irmsrsquo; absorptive capacity, trade orientation, firm siz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t the industry level by including in the analysis a competition control variable and the role of domestic firmsrsquo;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spillove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 addition, we use a unique dataset for Estonian manufacturing sector that provides us with very rich firm and industry level panel data (Jones and Mygind 1999).
We employ three alternative proxies for spillovers, and find that their magnitude varies with the proxy used, underlining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inward FDI generate different spillovers. In addition, spillovers depend on the recipient firmrsquo;s size, its ownership structure, domestic firm trade orientation and proximity to foreign firms. Moreover,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competition of both for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确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爱沙尼亚案例
Evis Sinani* and Klaus Meyer**
4月 2002年
初稿:2001年12月
外商直接投资(FDI)普遍被视为能在转型经济中为本土企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之前的研究仅衡量了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净影响,本文揭示了技术转移与竞争的积极作用,使用生产函数框架来估计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对1995 - 1999年期间爱沙尼亚国内公司产出增长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技术,控制行业和公司特定效应,并执行Heckman两阶段程序来控制样本自选偏差。
溢出效应的大小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和受援本地公司的特征而变化。溢出程度取决于作为代理人所使用的外国存在的衡量标准,并且由受援公司的规模、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向来调节。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受益于外国公司的竞争,因为竞争压力促使国内公司更有效地利用其现有技术,或寻找新技术以使其能够维持其市场份额。然而,外国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源于他们对合格雇员的猎头。因此,我们发现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本地公司有更高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受到该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
此外,我们的结果通过对具有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表现出不同影响,为企业转型文献做出贡献。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受益于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而内部人拥有的企业则经历了强烈的负面溢出效应。
关键词:溢出效应,技术转移,面板数据
JEL分类号:C23, D24, L11, L60, P31
介绍
对内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预期溢出效应促使许多转型经济体的政府采取旨在吸引投资者的政策。这些国家必须使其产业结构现代化,升级基础设施并获得新的能力,以繁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企业重组是经济转型的核心要素,也是转型经济体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Jones等,1998,Estrin和Rosevear,1998,Buck等,1998)。人们普遍认识到,外国直接投资在重建以前的中央计划经济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投资来源,可以克服国家部门崩溃和私营部门缓慢增长的局面,并提供新的管理技能、技术、资本和竞争(IMF等,1991,EBRD,1994,Meyer,2001),预计这些捐款不仅有利于外资企业,也有利于与外资企业接触的国内企业。
由于外国投资与先进技术相关,预计国内企业将受益于后向或前向联系和示范效应并从跨国公司(MNCs)获取现代技术。但是,国内公司也可能存在负外部性,例如,让熟练的员工失去跨国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增加东道国的竞争。 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大多数情况下的积极影响大于负面影响(UN 2001)。
学者们试图证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产业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为评估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到目前为止,发展中的结果(例如Haddad和Harrison 1993,Aitken和Harrison 1999)和转型经济(例如Djankov和Hoeckman 1998,Konings 2001)的结果好坏参半。然而,很少有研究在这些外部性发生的条件下探讨。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提供了关于技术溢出对当地公司生产力的大小以及有利于这种溢出效应的行业条件的新证据。
我们关注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影响同一行业中本地公司的产出增长。我们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些溢出效应是积极的吗?规模是多少?它们如何随着国内企业的特点而变化,如企业的吸收能力、贸易导向、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等?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在分析中包含竞争控制变量以及国内企业从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中获益的作用来研究竞争在行业层面的作用。此外,我们对爱沙尼亚制造业使用独特的数据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公司和行业级面板数据(Jones和Mygind 1999)。
我们采用三种替代代理来实现溢出效应,并发现它们的数量随使用的代理而变化,强调不同类型的内向FDI会产生不同的溢出效应。此外,溢出效应取决于受援公司的规模、所有权结构、国内公司贸易导向以及与外国公司的距离。国内公司受益于外国公司和其他国内公司的竞争,因为它促使他们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或者寻找新技术以保持其市场份额。反过来,这增加了他们获得溢出效益的能力。尽管熟练劳动力增加了公司的产出增长,但它向外国公司的转移显著降低了这种影响。此外,我们的结果通过对具有不同所有权结构的公司表现出有趣的不同影响,为企业转型文献(Estrin和Wright 1999)做出了贡献。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受益于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而内部人拥有的企业则经历了强烈的负面溢出效应。但是,只有局外人拥有的公司才有资源和能力赶上外国竞争对手。国家和外资公司的积极溢出效应也得到了竞争的支持。
2.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2.1 国际技术转让及其溢出效应
跨国公司生产、控制并拥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技术,全球私人研发支出中近80%由跨国公司负责(Dunning 1993,290)。通过鼓励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发展中国家希望向当地公司转让技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与母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有关(Kokko 1992,Blomstrom和Kokko 1996)。
技术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在国家之间转移,包括国际贸易、外国投资和合同转让。国际贸易转移商品中体现了新技术,例如差异化产品的新品种或资本品和设备。外国直接投资在一个跨国公司的边界内或外国公司与当地合资伙伴之间转移知识。合同协议可以将技术转换为知识产权的公平交易,例如以许可合同的形式。技术转让的类型和程度因技术本身的特征(例如年龄和复杂性)和东道国的特征(例如,教育水平、劳动技能、技术转让要求和竞争)而异。例如,Mansfield和Romero(1980)发现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附属公司的技术比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附属公司的技术要年轻,而许可和合资企业的技术比转让给附属公司的技术要早。因此,技术越现代化越复杂,跨国公司就越不愿意将其转让给第三方,而是转移到附属公司。此外,Kogut和Zander(1993)表明,隐性、可编辑性和可操作性等技术的属性决定了许可的可能性。他们的结果表明,技术越隐蔽,全资子公司转让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大。虽然可编码性和可教性提高了许可的可行性,但技术的复杂性是许可的一种威慑。然而,如果一家公司希望从其新的和复杂的技术中提取所有租金,他们可能会偏向外国直接投资(Caves 1996,World Bank 2000)。
仅在外资子公司中使用的技术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有限。然而,通过各种形式的溢出或外部因素,它可以在整个东道国传播。当一家公司的活动导致技术改进,从而导致另一家公司的生产力提高时,就会出现技术溢出效应,因此第一家公司无法获得其技术带来的所有好处。因此,技术转让的溢出效应可能通过四个主要渠道实现:示范模仿、国内雇员培训、竞争和后向联系。进入市场后的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展示其先进技术后可以实现技术转让的积极溢出效应,这些技术可能随后适应并模仿它们(Kokko 1992),当他们培训可能留给国内公司的国内员工时或通过向后——当具有先进技术的外国公司以较低的边际成本生产并因此从国内公司获得市场份额时,竞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国内生产力下降。特别是在短期内,竞争会对本土企业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Aitken和Harrison 1999)。然而,也可能是国内企业通过更有效地利用现有技术或通过投资新技术来维持其市场份额来应对外国竞争(Blomstrom and Kokko 1998)。
2.2 实证证据
通过技术转让给国内企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证文献包括对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研究。然而,这些文献提供了相当复杂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外国存在对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有积极影响,而其他研究则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或负面影响。
学者们使用两种方法来估算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行业水平数据或公司层面数据。对第一类研究通常会对国内企业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例如,Caves(1974)研究澳大利亚制造业,Globerman(1979年)研究加拿大制造业,Blomstrom和Persson(1983年)研究墨西哥制造业,1970年研究了外国存在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当地公司所有这些研究都根据汇总数据证实,各行业的溢出效应显著。然而,Kokko(1994)认为,溢出效应可能不会出现在所有行业中,特别是如果外国公司在“飞地”运营,即与国内公司隔离。他利用墨西哥制造业的一个横截面,发现在国外市场份额较高且生产力差距较大的行业中没有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没有这些特征的行业表现出外国存在与当地生产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使用公司层面数据的第二类研究没有为国内公司提供溢出效应或负面证据。例如,Haddad和Harrison(1993)研究了外国存在对当地公司相对生产率的影响(即将公司层面的生产率与行业中最佳实践公司的生产率进行比较)。利用摩洛哥的数据,他们没有发现溢出效应的证据。然而,竞争似乎促使本地公司走向技术水平较低的行业的最佳实践前沿。因此,溢出并不总是发生在所有工业部门。Aitken和Harrison(1999)发现了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称为“市场窃取效应”,即外国投资通过迫使国内企业减产来短期内降低国内工厂的生产率。此外,他们还测试了溢出效应是“本地”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主张。
Kokko、Tasini和Zejan(1996)使用乌拉圭制造业的企业级数据来研究个体工厂的生产率(而非行业平均值)如何受到外国存在的影响。根据技术差距的大小将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他们发现溢出效应仅在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中显着。如果差距很小,外国技术似乎对本地公司更有用,因为他们拥有应用或学习外国技术所需的技能。相比之下,Sjoholm(1999)仅在具有较大技术差距的子样本中发现了对国内企业溢出效应的证据。此外,他发现很大程度的竞争会增加溢出效应。
转型经济研究仅在近几年才出现。Djankov和Hoeckman(1998),Yudaeva等(2000),Kinoshita(2000)和Konings(2001)基于企业层面数据调查转型经济体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而Zhang(2001)使用来自中国地区的数据。大多数这些研究的结论与先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企业没有或有负溢出效应的结果一致。例如,Yudaeva等人(2000)没有找到关于本地溢出效应的证据,然而,与Aitken和Harrison(1999)相比,他们发现中等规模企业具有强大的积极溢出效应,这些企业主导了小企业的负面溢出效应。与Yudaeva等人相反。Konings(2001)的结果与Aitken和Harrison(1999)一致。他发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国内企业存在负面溢出效应,这表明竞争的负面影响主导了技术转让的积极影响。相比之下,他没有发现波兰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的证据。Djankov和Hoeckman(1998)使用1992-1996年期间捷克共和国的公司层面数据发现,公司规模、劳动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等公司特征似乎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考虑到这些因素并利用国外和国内公司的整个样本,作者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影响虽然微不足道,但影响微不足道。虽然只关注国内企业,但他们发现了消极和重大的溢出效应。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其他技术转让渠道,如贸易渠道(以进口渗透率衡量)对捷克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与所有这些研究不同,Zhang(2001)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让的积极溢出和促进转型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这些溢出效应在内陆地区比内陆地区更大。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正溢出效应的文献中的不同推论主要是使用综合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的结果。在使用行业而非公司的横截面数据的研究中,外国份额系数被解释为溢出效应的衡量标准。然而,行业层面的总体数据无法控制各部门的生产率差异,这可能与外国存在相关。换句话说,外国存在与国内企业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可能部分归因于外国企业投资于更具生产力的产业。这个问题被称为内生性问题,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导致溢出系数向上偏差。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一组公司级数据,这使我们能够控制内生性和选择偏差。
2.3 研究方法
先前的理论和实证文献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可能会增加或降低同一行业内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主张是存在溢出效应,我们的目标是确定其方向和规模。之前的研究只测量了技术转让的积极影响和竞争的负面影响之间的净效应,这两者都源于外国市场进入市场。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使用技术和竞争控制变量来解决技术转移与竞争的影响。
其次,文献表明,溢出效应随当地公司的特点而变化。为了解释溢出效应的原因,我们的目标是确定解释国内公司对外国公司进入的反应的特征、随之而来的竞争变化,以及外国投资公司采用的更高技术水平。因此,我们将无形资产投资、新机器设备投资和劳动力质量作为企业层面的创新措施,投资新技术以取代过时的资本和劳动力运营新技术的能力。无形资产的定义包括技术知识、品牌名称、专利、管理技能、营销和出口网络以及声誉,这些都是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元素。此外,正如Teece(1977)强调的那样,无形资产更有可能以合理的成本转让给子公司,而不是通过向独立公司发放许可。
此外,我们还分析了这些企业特定变量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相互作用。Cohen和Levinthal(1989)认为,R&D有两个“面孔”:它不仅模拟创新,还提高了公司的吸收能力,即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这种吸收能力是通过无形资产与具有溢出变量的新机器和设备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的。
劳动力质量与外国存在在行业层面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国内企业的影响。通过转向国内公司,技术工人带来了外国公司先进技术的知识,这可能会导致技术的提高,从而提高国内公司的生产率。Borensztein等人(1998)包括人力资本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相互作用项,以说明一个国家需要人力资本从外国直接投资中受益的事实。他们发现,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825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饮用水微生物群:一个全面的时空研究,以监测巴黎供水系统的水质外文翻译资料
- 步进电机控制和摩擦模型对复杂机械系统精确定位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具有温湿度控制的开式阴极PEM燃料电池性能的提升外文翻译资料
- 警报定时系统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调查驾驶员信任的差异以及根据警报定时对警报的响应外文翻译资料
- 门禁系统的零知识认证解决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车辆废气及室外环境中悬浮微粒中有机磷的含量—-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协议对城市风力涡轮机的无线监控: 支持应用软件和传感器模块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系统在医疗保健中提供位置信息和传感器数据传输的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PLC的模糊控制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外文翻译资料
- 光伏并联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独立应用程序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