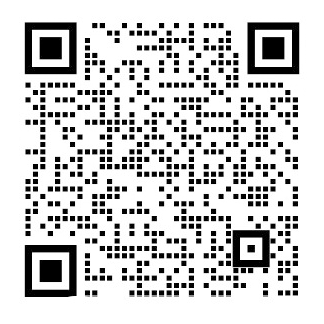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 国内研究
1.五四以来“新女性”形象
学者姚玳玫的博士论文整理成书《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于200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研究时间段是从晚清到整个民国时期,运用叙事学的想像理论并站在文化/性别想象的角度解读海派小说中形形色色女性形象。除了文本挖掘与理论支撑,作者也注重加入史料旁证。书中第二部分“想像”与“女性”共有八章:中国近、现代小说叙事中的海派“另类”、想像女性:《海上花列传》的叙事、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海派小说的言情定位、肉欲趣味与波皮垮掉:海派女性想像的新旧转型、从“唯美”到“摩登”:城市际遇中的现代女性、日常生活价值的重建与平民女性形象的构型、海派女性书写的登台、海派女性书写的成熟与张爱玲的女性构图。在探讨女性群像的同时不仅包含有与城市现代性的关系,也有在形象构建中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对于了解自民国到如今“新女性”形象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者杨联芬《在解放的困厄与反思——以20 世纪上半期知识女性的经验与表达为对象》中探讨了在五四运动以后妇女解放被纳入社会解放工程之后女性面临的困境——“个人”与“女人”的冲突。谈及冰心与陈学昭在当时情境下所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虽不成熟但确实体现了当时欧风美雨加之五四解放思潮下的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的发展。
- 女性向文学研究
在知网检索到“女性向”共有62条,其中涉及较多的领域为网络小说。如吴小玲和张霄在《天府新论》上发表的《虚假的觉醒:“种田文”中的女性意识探析》是对时下流行的种田文进行深度分析,发现看似处处彰显女性意识的“觉醒”其实是假的,这种困境由来已久——近现代丁玲、冰心、陈染等的写作到现代网络女性写作都始终无法走出桎梏。肖映萱在《“女性向”网络文学的性别实验——以耽美小说为例》中分析在日本压抑女性的文化氛围下发展出的“女性向”文化在传入中国后经历的性别实验,并以“耽美”小说为例说明当下网络女性主义所引发的革命是确实发生且在消除一些性别界限了。
检索“女性写作”共有3046条,但其中关于中国的只有205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乔以钢的《在实践和反思中探索前行———近 20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简论》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并且汲取和借鉴了女性主义以及其他多种理论资源对近20年以来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进行了挖掘与整理。胡明贵的《女性主义思潮与20 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互动关系检讨》辨析了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浪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与利弊。王玉琴在《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历程及史观演变》中将百年中国女性文学史分为“五四”前后、“三四十年代”、“建国十七年”、“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十年”五个阶段,发现在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引入与反思中新时期以来的女书写更偏重于情感与自我存在意识的探讨。李秀萍的《新时期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中探讨的是多元思潮下女性写作开始建构起鲜明的性别特征。通过这四篇文献可以大致把握西方女性主义传入中国本土化进程的特征。
检索“网络女性主义”共有46条记录,由于近年来网络才得以快速发展,所以在此方面能查到的文献并不多。肖映萱、叶栩乔的《“男版白莲花” 与 “女装花木兰”—— “女性向”大历史叙述与“网络女性主义”》是以2016年一部火爆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琅琊榜》为例分析出研究对象,因为该小说出身于“女性向”网站 且有“女性本位”意识。如其中的“女装花木兰”就是女性视野中的女性想象,不同于传入中国本土的西方女性主义,而是在网络空间中自发形成的,具有草根性与民间性。薛静的《从“总裁爱我”到“我即总裁”:网络言情小说更迭》认为网络言情小说中早期的 “总裁爱我”,发展到现在的“我即总裁”(即“大女主”的想象),正是网络女性主义的发展源泉。
检索“种田文”共有8条结果,因为《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属于种田文,所以对此类网文进行了解也是十分有必要的。李昊的《新世情小说的复兴———浅谈“种田文”的走红》认为种田文拥有通俗简练的白话文风、严谨真实的细节描写与整齐清晰的章回叙事,其走红代表着现代人对悠闲田园生活的一种追求,也是目前审美多元化转型的体现。
(二)西方研究
不得不承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谈及“女性主义”,我们的认知大多还停留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层面上。不少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世界的路径。因而在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不够成熟时,对西方女性主义进行了解,在时代语境下分析其对中国的影响便成为本文研究的必然。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锋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Gender Performativity Theory不同于波伏娃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二分法。她对于女性主义的贡献正在于她在研究波伏娃理论的基础上解构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be)女人,她在社会中成为(become)女人”这个观点,从而比波伏娃走得更远。也即是说,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一样,都是位于象征界的社会建构,纯粹意义上的分离其实并不存,因为表演性是建构/重建主体的重要途径。在她的《性别麻烦》与《身体之重》中,她并不跟随之前的“本质论”(“生理即命运的”),也不认同建构论中的“后天形成的女人”,而是对这个性别本身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比如在她的眼里,异性恋只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结果,而这种反叛的意义在于从结构内部打破固有认知,从而在思想意识与社会文化层面唤醒了更深的思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其实是在某种固有框架与权威中多次操演得来的结果。对他者的包容带来的是一种更为开放的视角,她并非是反女性主义,而是在多元性别的立场上给予女性以更多的可能性,让她们有更多审视自己的机会。
(三)对象研究
在知网检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并无关于该小说或电视剧的研究,所以主要是从文本自身出发。作为研究对象的网络小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作者在谈及书名时说“短短几句词,描绘出一个古代贵族女子悠闲洒脱的生活场景。我很喜欢在这种生活状态,很自在,很慵懒,希望明兰也是如此。”这一句大致点明了本书的性质,即种田文。作为女性向网络文学的一种类型,它首先是由女性作者创作,出发点与立场自然是倾向于女性自身的;其次,种田文也称家长里短文,大多是以古代封建社会为生活背景,描写主人公及其家人日常衣食住行、鸡毛蒜皮等生活琐事,这种类型的作品,多为女性读者所接受。在张霄的《“种田文”中受众的心理与行为研究》中,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全球最大的女性文学基地晋江文学城进行研究讨论,得出结论是“受众选择阅读lsquo;种田文rsquo;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受众lsquo;爽rsquo;的需求,并且由于lsquo;种田文rsquo;与现实社会有着相似或相通的经验空间,从而产生极大的lsquo;认同rsquo;和lsquo;代入感rsquo;,使得读者对该类文本进行选择性理解和记忆,而对文本的选择性理解和记忆又使得读者产生极大的lsquo;认同感rsquo;和lsquo;代入感rsquo;,从而跟随主角近距离感受那种lsquo;够得着的成功rsquo;。联系现实,读者对这种lsquo;够得着rsquo;的lsquo;爽rsquo;的追求实际上与现代女性生活压力大、对未来抱有幻想和期待有关。”[1]所以种田文总体来说是以女性意愿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