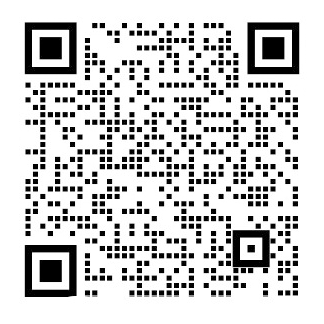文献翻译原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20131374013 翻译一班 李宜洁
Extracted from Translation Studies(third edition),which is written by Susan Bassnett, Susan Bassnett is the leader of the School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 Centre for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rwick. The excerpt is from the 22nd page to the 23rd page and the 38th page to the 44th page and the 82nd page to 83rd page.
节选自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第三版, 苏珊·巴斯奈特是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是翻译方面比较文学研究的教授和华威大学比较文化研究的中心人物。节选了第22页到第23页,38页到第44页以及82页到83页的内容。
the 22nd page to the 23rd page: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 first step towards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must be to accept that although translation has a central core of linguistic activity, it belongs most properly to semiotics, the science that studies sign systems or structures, sign processes and sign functions (Hawkes,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London 1977).Beyond the notion stressed by the narrowly linguistic approach, 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the transfer of lsquo;meaningrsquo; contained in one set of language signs into another set of language signs through competent use of the dictionary and grammar, the process involves a whole set of extra-linguistic criteria also.
Edward Sapir claims that lsquo;language is a guide to social realityrsquo; and that human beings are at the mercy of the language that has become the medium of expression for their society. Experience, he asserts,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language habits of the community, and each separate structure represents a separate reality:
No two languages are ever sufficiently similar to be considered as representing the same social reality. The worlds in which different societies live are distinct worlds, not merely the same world with different labels attached.
Sapirrsquo;s thesis, endorsed later by Benjamin Lee Whorf, is related to the more recent view advanced by the Soviet semiotician, Juriacute;Lotman. That language is a modeling system. Lotman describes literature and art in general as secondary modeling systems, as anindication of the fact that they are derived from the primary modeling system of language, and declares as firmly as Sapir or Whorf that lsquo;No language can exist unless it is steeped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and no culture can exist which does not have at its center, the structure of natural language.rsquo; Language, then, is the heart within the body of culture, and it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hat results in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energy. In the same way that the surgeon, operating on the heart, cannot neglect the body that surrounds it, so the translator treats the text in isolation from the culture at his peril.
the 38th page to the 44th page :
LOSS AND GAIN
Once the principle is accepted that sameness cannot exist between two languages, it becomes possible to approach the question of loss and gain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is again an indication of the low status of translation that so much time should have been spent on discussing what is lost in the transfer of a text from SL to TL whilst ignoring what can also be gained, for the translator can at times enrich or clarify the SL text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oreover, what is often seen as lsquo;lostrsquo; from the SL context may be replaced in the TL context, as in the case of Wyatt and Surreyrsquo;s translations of Petrarch.
Eugene Nida is a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blems of loss in translation, in particular about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the translator when faced with terms or concepts in the SL that do not exist in the TL. He cites the case of Guaica, a language of southern Venezuela, where there is little trouble in finding satisfactory terms for the English murder, stealing, lying, etc., but where the terms for good, bad, ugly and beautiful cover a very different area of meaning. As an example, he points out that Guaica does not follow a dichotomous classification of good and bad, but a trichotomous one as follows:
- Good includes desirable food, killing enemies, and chewing dope in moderation, putting fire to onersquo;s wife to teach her to obey, and stealing from anyone not belonging to the same band.
- Bad includes rotten fruit, any object with a blemish, murdering a person of the same band, stealing from a member of the extended family and lying to anyone.
- Violating taboo includes incest, being too close to onersquo;s mothering-law, a married womanrsquo;s eating tapir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first child, and a childrsquo;s eating rodents.
Nor is it necessary to look so far beyond Europe for examples of this kind of differentiation. The large number of terms in Finnish for variations of snow, in Arabic for aspects of camel behavior, in English for light and water, in French for types of bread, all present the translator with, on one level, an untranslatable problem. Bible translators have documented the additional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for example, the concept of the Trinity or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parables in certain cul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lexical problems, there are of course languages that do not have tense systems or concepts of time that in any way correspond to Indo-European systems. Whorflsquo;s comparison (which may not be reliable, but is cited here as a theoretical example) between a lsquo;tem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译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20131374013 翻译一班 李宜洁
节选自苏珊·巴斯奈特的《翻译研究》第三版,苏珊·巴斯奈特是是文化翻译学派的领军人物,是翻译方面比较文学研究的教授和华威大学比较文化研究的中心人物。节选了第22页到第23页和第38页到第44页以及82到83页的内容。
第22页到第23页:
语言和文化
对于翻译过程的检查,首要的一步是必须理解:尽管翻译有着语言活动的核心,但它属于符号学更恰当,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系统或结构,符号处理和符号函数的学科(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伦敦1977)。超出了狭隘的语言方法强调的概念,符号学认为通过充分使用字典和语法,翻译涉及将蕴含在一套语言符号中的“含义”转移到另一套语言符号中,这个过程也涉及一整套额外的语言标准。
爱德华·萨丕尔宣称“语言引导了社会现实”并且人类在他们的社会里已被表达的媒介所掌控。他断言,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群体的语言习惯决定的,并且每一个单独的结构代表了一个单独的现实:
没有两种语言曾被视为非常相似而代表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社会所存在的世界是明显不同的世界,不仅在被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世界。
萨丕尔的理论,后得到本杰明·李·沃尔夫的认可,与前苏联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提出的更先进的最近的观点有着联系。这个更先进的观点就是语言是一种建模系统。洛特曼笼描述了文学和艺术作为第二建模系统,并声称事实表明它们是源于语言的第一建模系统,而且像萨丕尔或沃尔夫那样坚定宣布:“没有语言可以存在除非它沉浸在文化语境中;没有其中心的文化不可能存在,中心就是自然语言的结构。”语言,就是文化主体的心脏,并且是能产生生命能力的延续的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医生也是一样,做心脏手术,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肉体,所以译者脱离文化孤立看待文本是冒险的。
第38页到第44页
丢失与得到
两种语言之间不能存在同一性,接受了这一原则,就可以在翻译过程中处理丢失与获得问题。 这再次表明翻译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不高,大量时间应该花在讨论将文本从SL转移到TL而丢失的东西上,与此同时忽略可以获得的内容,因为译者时时可以丰富或阐明SL文本是翻译过程中的直接结果。此外,经常被认为是从SL语境中“丢失”的内容可能在TL语境中被替换,就像怀特)和萨里翻译的《皮特拉克》一样。尤金·奈达的翻译是翻译中关于“丢失”问题的丰富来源, 特别是当翻译人员面临在SL中术语或概念不存在于TL这样的困难时。他以Guaica(委内瑞拉南部一种语言)为例,在该语种很容易找到与英语中谋杀,偷窃,撒谎相对应得词条,但是像好的,糟糕的,丑陋的,美丽的这些词条去却是覆盖了不同意义领域 例如,他指出,Guaica不遵循好坏的二分法,而是三分法:
- 好的条目,包括理想的食物,杀死敌人,适度咀嚼,给妻子点火,教她服从,偷窃其他不与他同伙的人。
- 坏的条目,包括腐烂的水果,任何有瑕疵的物体,谋杀同伙,窃取大家庭成员,向人撒谎。
- 违反禁忌行为包括乱伦,和婆婆过于亲近,已婚妇女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吃貘,还有孩子吃老鼠。
这种差异化的例子,在欧洲也有非常多。芬兰语中有大量的词语去描述雪花,阿拉伯语中有大量词语去表述骆驼的行为,英语中有大量的词去描述的光和水,而法语中有大量的词语表示的面包类型,在某一个层面上,这些都使翻译者面临着不可译的问题。圣经的译者记录了一些额外的困难,涉及到例如三位一体概念,或比喻在特定文化中的社会意义。当然,除了词汇问题之外,语言没有严谨的时间系统或概念完全符合印欧系统。“时间语言”(英语)与“永恒的语言”(霍皮语)之间的沃尔夫比较(这可能不可靠,但被称为理论示例)阐明了这一方面。
不可译性
当译者遇到这样的困难,就提出了整个文本的可译性问题。卡特福德区分了两种不可译性,语言和文化。在语言层面上,在SL中没有词法或语法替代SL词条时,就会出现不可译性。那么,例如,德国的“Um wieviel Uhr darf Sie morgen wecken?”或丹麦 “Jeg fondt brevet”在语言上是不可译的,因为这两个句子所涉及的结构在英语中。然而,一旦应用英语结构的规则,两者都可以完整翻译成英文。翻译者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两句话翻译成“你明天几点起床?”和“我找到了这封信。”,调整了德文语序,并调整了丹麦语文章中后置词的位置,以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卡特福德语言的不可翻译性的范畴,Popovič也曾提过,简单易懂,但他的第二类范畴,就有点晦涩。他认为,语言的不可译翻性是由于SL和TL的差异,而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由于TL文化中没有SL文本的相关情境特征。他以“浴室”在英语,芬兰语或日语语境中的不同概念为例,说明其所指对象和该对象的使用者都不一样。但是,卡特福德还称,一些更为抽象的词条,如英文术语“民族”或“民主”是可译的,并且认为“我将要回家”的英语短语,或者“他在家”可以在大多数语言中进行对等翻译,就好像“民主”这个词是国际化的一样。
现在,在某个层面上,卡特福德是对的。英语短语可以翻译成大多数欧洲语言,并且民主是国际惯用的术语。但他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这似乎代表了一个过分狭隘的不可译性的问题。如果“我要回家”,翻译成 “Je vais chez moi”,SL语句的内容意义(即根据自我意识进入居住地点和/或起源)只是被大概地复制。例如,如果一个暂时在伦敦的美国居民说这个词,那么这可能意味着要回到现在正在居住的“家”,这个区别必须用法语来界定。此外,英文术语家庭,如法国门厅,具有一系列关联意义,不能用更局限的词语 “chez mo”来翻译。因此,对于“家”的翻译似乎会出现与翻译芬兰或日本“浴室”完全相同的问题。 对“民主”的翻译,也出现更多的复杂性。
卡特福德认为,这个术语主要存在于许多语言的词汇中,虽然它可能与不同的政治情况有关,但背景将指导读者选择适当的情境特征。这里的问题是,读者会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来形容这个词的概念,并将相应地应用这个特定的观点。因此,在以下三个短语中出现的的形容词 “民主”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概念:美国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英国保守党的民主党。所以尽管这个术语是国际性的,但其是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表明,(即便曾经有过)现在已经不存在任何共同的背景以供选择相关的情境特征。如果我们认为文化是动态的,那么社会结构的术语也必须是动态的。洛特曼指出,文化的符号学研究不仅将文化功能视为一种标志体系,而且强调“文化与标志和意义的关系与其基本特征之一是一体的。”卡特福德从不同的前提开始,并且因为他对语言和文化的动态性研究不够深入,所以他让自己的文化不可译性的类别无效。就目前所及,语言是文化中的主要建模系统,在任何翻译过程中,必须真正隐含文化的不可译性。
达贝尔内和维奈在他们的实用书“比较 法语-英语 风格”中分析了两种语言之间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区别了尝试在没有分离语言和文化的前提下定义不可翻译性的构成区域。 Popovic也区分了两种类型。第一个定义为:
语言元素在结构,线性,功能或语义方面不能被充分替代的情况,因为缺乏指称或内涵。
第二种类型超出了纯粹的语言学:
表达意义的关系,即创意主体与原文中的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没有找到足够的语言表达的情况。
第一种类型可能被看成与卡福德语言不可翻译性的类别平行,而在第二种类型中,诸如 Bon appetit或丹麦语中的有趣系列日常词语用来表达谢意。 Bredsdorf 的丹麦语言为英语读者提供了详细的细节上下文使用这种表达。对“疯子”这个词的解释,例如说,“客人或家庭成员餐后,主持人或女主人没有这种表达方式的英文等同词。”
翻译意大利语中的句子Cst stato un tamponamento的情况更为困难。
由于对于英语和意大利语在组成部分和单词顺序来说足够接近于句法组织的近似模式,所以该句子完全可以翻译。概念层面也是可以翻译的:现在报道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个难题涉及意大利名词的翻译,它要以英名词短语的形式出现。TL版本允许英文和意大利语句的差异:“这里发生过一个小事故(过去完成时,这里发生了一个小事故(一般过去时)。”(涉及车辆)。
由于时态的差异,根据句子的上下文,TL句子可以采用两种形式的其中一种,并且由于名词短语的长度,这也可以被削减,只要接收者能在句子之外确定事故的性质就可以了。但是,当认为tomponamento的意义等同于意大利整个社会时,如果不了解意大利的驾驶习惯,发生“轻微事故”的频率以及这种事件的权重和相关性,那么,就不能完全理解该术语。简而言之,tomponamento是一种具有文化约束或语境意义的标志,即使用说明性的短语也不能翻译。 因此,创作主体与其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不能在翻译中得到充分的替代。Popovič的第二个类型,如卡特福德的次要类别,说明了描述和定义可折叠性限制的困难,但是卡特福德的理论从语言学开始时,而Popovič从一个涉及文学交流理论的角度开始。莱万德夫斯基)在一篇他试图总结翻译研究和符号学的文章中,认为卡特福德与现实脱离了现实,而乔治·莫恩认为,过分关注不可译性,从负面影响了翻译人员处理的一些不得不处理的实际问题。穆南认识到语言学进步对翻译研究带来的巨大好处;结构语言学的发展,索绪尔,叶姆斯列夫的作品,莫斯科和布拉格语言圈的工作一直是非常有价值的,乔姆斯基和转型语言学家的工作也受其影响,特别是在语义研究方面。穆南认为,由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并且必须)接受:
(1)个人经验的独特性是不可译的。
(2)理论上,任何两种语言(例如音素,语素等)的基本单位并不总是可比的。
(3)考虑到演讲者和听者,作者和翻译者的各自情况时,可以进行沟通。
换句话说,穆南认为,语言学表明翻译是一个可以相对成功完成的辩证过程:
翻译总是可以从最清晰的情况,最具体的信息,最基本的普遍性开始。但是,由于它涉及到语言整体性的考虑,与其最主观的信息一起,通过检查共同的情况和倍增的需要阐明的联系,毫无疑问,通过翻译的沟通是无法完全完成的,同时表明,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已经明确表明,找到解决最困难的问题的办法是翻译者的任务。那么这解决方案可能有很大差异;翻译者对于是什么构成不变信息给定的参考系统的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李维强调翻译中的直观要素:
在所有的符号学过程中,翻译也具有务实的维度。翻译理论往往是规范性的,在OPTIMAL解决方案上指导翻译者;实际的翻译工作是务实的,翻译人员了找到了以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可行方案之一。也就是说,他直观地解决了所谓的MINIMAX策略。
第82页到第83页:
文学翻译的具体问题
在介绍这本书时,我觉得有必要密切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不试图理解翻译过程背后的方式的译者就像劳斯莱斯的司机不知道怎么让车子开动。同样,花了一生的时间拆卸发动机却从未出去在路上开过车子的技工就像一位书呆子般的学者以破坏的代价来探究怎样成功的过程。因此,在这第三版中提议通过进一步的实例分析来探讨文学作品翻译的问题,不是要过多评价作品而是表明翻译的具体问题可能由于个别译者的标准选择而出现。
结构
安妮·克鲁申纳尔,在她有关文学文体学的书中,发表了一些关于翻译的要点。她认为译者在决定保留源语文本时不应遵从笼统的感觉,但应留意每个单独的结构,无论是散文或诗,因为每一个结构都会注重某些语言特征和水平而不是其他东西。她继续分析塞西尔·戴·刘易斯对的瓦莱里的诗的翻译,最终得出结论,翻译不成功是因为译者在翻译时没有带着文学翻译的充分的理论。她觉得,戴·刘易斯的翻译忽视了部分对个体和对整体的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一个典型的lsquo;差rsquo;的案例”。也提出了对这种不足的补救措施:需要什么,克鲁申纳尔认为,“是对每个单独的要翻译的作品的主流结构的描述。”
克鲁申纳尔关于文学翻译的陈述清楚地基于将包含的文本作为一套相关系统,与其他系统共同运作的文学文本的一个结构主义方法。正如罗伯特斯科尔斯所说的:
来自单个句子的每个文学词汇相对于整个句子的顺序可以被看成是与系统概念有关。尤其,我们可以将个人作品,文学体裁,和整个文学视作为相关的系统,并将文学看作是人类文化的更大系统中的系统。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614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饮用水微生物群:一个全面的时空研究,以监测巴黎供水系统的水质外文翻译资料
- 步进电机控制和摩擦模型对复杂机械系统精确定位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具有温湿度控制的开式阴极PEM燃料电池性能的提升外文翻译资料
- 警报定时系统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调查驾驶员信任的差异以及根据警报定时对警报的响应外文翻译资料
- 门禁系统的零知识认证解决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车辆废气及室外环境中悬浮微粒中有机磷的含量—-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协议对城市风力涡轮机的无线监控: 支持应用软件和传感器模块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系统在医疗保健中提供位置信息和传感器数据传输的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PLC的模糊控制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外文翻译资料
- 光伏并联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独立应用程序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