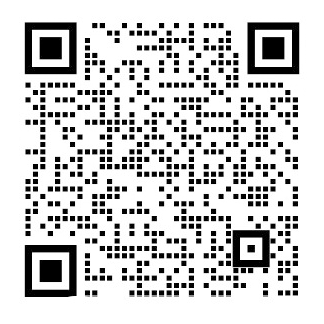行为金融框架下的汇率
Paul De Grauwe, Marianna Grimald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保罗bull;德bull;格劳威(Paul De Grauwe)和玛丽安娜bull;格里马尔迪(Marianna Grimaldi)合著的《行为金融框架下的汇率》(The Exchange Rate ina Behavioral Finance Framework)一书,对汇率动态提出了新的见解。“盒子”是人们熟悉的“理性预期-有效市场”模型,作者指的是国际宏观经济学中存在已久的一套主流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货币/投资组合平衡模型,以及Obstfeld和Rogoff(1995)的跨期优化模型。相反,作者检验了一个基于Frankel和Froot(1986)原始的基本面-技术面汇率模型。该模型只包括投机者,他们以两种方式进行预测:“基本面分析师”推断过去的变化,而“技术面主义者”总是期待基本面的回归。
作者从不羞于表达他们的动机:他们将第一章命名为“对新模型的需要”,并将他们对模型的介绍命名为“替代方法的大致轮廓”。他们提醒我们,主流模型在预测汇率动态方面几乎没有价值,也无法解释许多反常现象,包括汇率的繁荣-萧条周期、长尾收益率、波动性聚集以及汇率与基本面之间的明显脱节。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基本面-技术面汇率模型,正如书中所示,该模型可以解释所有这些异常现象。
这篇综述提出了两个问题。问题1:DeGrauwe和Grimaldi认为是时候寻找新的汇率模式了,这一观点正确吗?由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意这一观点,这份报告让库恩成为了一名公正的法官。他的见解表明,答案是肯定的。问题2:这本书有可能促成它所期望的模型转变吗?评论的回答是:不。有充分的科学理由将基本面-技术面二分法纳入下一个模型。然而,该模型本身似乎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因为它在内部是不一致的,其其余的基础结构也与证据不一致。
是时候寻找新的汇率模式了吗?科学革命方面最著名的权威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指出,科学革命通常始于反常现象的出现——比如那些长期困扰汇率经济学家的现象(库恩,1970年)。正如库恩所述,模型和证据之间的冲突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主流模型产生怀疑,并对现存的模型追随者提出挑战。旧模型未能解释异常现象,导致研究人员越来越“焦虑”,并最终引发一场“危机”。模型怀疑论者在汇率经济学中并不难找到。除了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一长串对主流模型持批评态度的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一些杰出人物,如库里、古德哈特、弗兰克尔、加利、吉奥瓦尼尼、弗拉德、罗斯、泰勒、埃文斯和莱昂斯。强化汇率经济学中的焦虑心理与库恩所讨论的自然科学模型不同,支配模型从来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支持证据(Meese and Rogoff, 1983;巷,2001)。
根据库恩的说法,信徒和怀疑者对严格的科学探究的定义不同,因此,他们经常互相讨论。信徒们认为模型之外的任何研究都是科学上的不负责任,而怀疑论者则致力于探索新的科学领域,因为他们认为研究对他们来说是失败的模型没有任何意义。这些现象也可以在今天的汇率经济学中找到。今天,对汇率经济学持怀疑态度的人通常会将主流汇率模型的微观基础作为其致命弱点——但这正是其追随者最欣赏的模型的方面。这些微观基础的内在一致性有助于这种模型避免在一个重要维度上的随意性,而这个维度曾困扰过早期的汇率模型。怀疑论者同样重视内在的一致性,但他们认为这些微观基础在另一个维度上是特别的:它们充其量只是与现实微弱地联系在一起。在怀疑者看来,研究人员可以分析无限多的想象世界,但科学的挑战在于解释真实世界。在应对这一挑战时,一个内在一致但与现实极不一致的模型可能没有什么价值。
如今对汇率持怀疑态度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详细阐述他们的担忧,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主流模式中有关持续购买力平价和利率平价的假设与宏观经济现实完全相悖。20世纪90年代,怀疑者的关注点扩大到主流模型的微观结构与外汇市场微观经济现实之间没有任何对应关系,就像在交易大厅、资产管理公司和公司债券上观察到的那样。(Goodhart(1988)和Frankel等人(1996)对此进行了阐述;市场现实在Rime(2003)和Sager and Taylor(2006)中有所描述。例如,主流模型长期以来一直假设,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汇率对新闻的反应不需要进行交易,但这两个假设现在都与“汇率的新微观经济学”(Lyons, 2001)的大量证据相矛盾。
德bull;格劳威和格里马尔迪对主流模型的第三个方面提出了异议,即投机者是完全理性的。在这里,再一次,经验证据站在怀疑论者的一边。理性预期的假设长期以来与来自心理学的证据相冲突(Yates, 1990),也很难与来自国际经济学本身的证据相一致(MacDonald, 2000)。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理性预期的假设也与行为金融学的最新证据相冲突。事实上,到1980年,普通人完全理性的正常失败已经如此确定,以至于前沿心理学家开始询问,人们是否能够克服他们的认知偏见(例如,Hoch, 1985)。在外汇市场上,即使是边际代理人也明显是非理性的:作为一个群体,外汇交易商似乎明显过于自信,而且没有表现出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趋势(Oberlechner和Osler, 2006)。
在指出理性预期假设是反事实的过程中,德bull;格劳威和格里马尔迪令人钦佩地以最纯粹的形式完成了波普尔(1959)的科学探究议程,该议程涉及到对现有模型的篡改。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是非常勇敢的。即使在金融领域,人们对行为研究的反应也是褒贬不一,而在国际经济学领域,这样的研究也不受欢迎。的确, Frankel和Froot已经试图通过强调这个模型的行为基础来获得广泛的支持,但收效甚微。
库恩认为,正如德bull;格劳威和格里马尔迪所言,汇率经济学正处于一场科学革命之中,这似乎是公平的。然而,库恩强调,一个主导的模型只能被一个有大量经验支持的新模型取代,而寻找新模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他们的书中,德·格劳威和格里马尔迪试图为他们喜欢的挑战者争取支持。这种尝试本身就会招致追随者的不屑,但正如库恩所言,这种努力从本质上就值得尊重,因为在主流模型下的研究——尽管困难而重要——只相当于“扫尾”。
尽管如此,我们仍必须追问:在行为金融框架下的汇率,是否可能促使模型转向基本面-技术面汇率模型?为了对模型进行评价,需要对模型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模型中的投机者根据滞后的风险调整回报来选择是做图表分析师还是原教旨主义者,因此他们在不同类型之间的配置是不断变化的。由于市场的结构依赖于这种分配,代理人可能无法始终了解这种结构,这是排除理性代理人的一个重要理由。该模型中的均衡要求外国债券的股票需求与股票供应相等。均衡汇率汇总了各代理的不同预期,Frankel和Froot(1986)提出了一种方法来替代他们自己的“投资组合经理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经理选择单一预测作为可用预测的加权平均值。模型中的利率是外生的,基本汇率也是随机游走的。由于该模型是高度非线性的,其性质是通过仿真得到的。
第二章介绍了模型的玩具版,突出了关键直觉;严肃的版本在第三章中介绍。接下来的几章将介绍额外的复杂性,如内源性风险规避、交易成本和内源性外国资产供应。第8章为模型的预测提供了经验证据。最后几章考虑了该模型的混沌特性,并将其应用于外汇干预。
该模型有三个显著的优点。首先,有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图表分析师和原教旨主义者在外汇市场都很活跃。根据对专业汇率预测的大量调查(例如,Frankel和Froot, 1987, 1990),这些类型的存在在1980年代中期成为一种程式化的事实。随后的研究继续描绘了一个一致的画面(MacDonald(2000)提供了一个最近的调查)。外汇市场参与者声称,技术分析——可能涉及外推预测,也可能涉及回归预测——是他们做出短期交易决定的关键指导。许多其他市场参与者声称他们的预测是基于基本面的,从而为均值回归预期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例如,张和Chinn, 2001)。
该模型的第二个优点是,它为许多常见的汇率异常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该模型具有多重平衡,其中一些是非基本的。汇率在基本均衡和非基本均衡之间波动,而且,由于该模型对初始条件表现出敏感性,汇率波动的时间和幅度在现实中基本上是不可预测的。因此,该模型与“汇率脱节之谜”以及美元在浮动汇率下的大幅波动是一致的。浮动汇率是另一种抗拒主流模型解释的现象(Flood and Rose, 1995)。模拟表明,当原教旨主义者不愿进行推测,而图表分析师进行更积极的推测时,非基本平衡更有可能发生。
该模型的非线性产生了特定区域的汇率动态,这让人想起了当前对购买力平价的分析(例如,Chowdhury et al., 2004)。例如, 在平静时期,汇率倾向于接近其基本价值,徘徊在交易成本决定的范围内。在不稳定时期,速率可以趋向于一个非基本的混沌吸引子。
该模型的第三个优点是它的一些关键结论具有普遍性。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理性的行为人,大幅波动的趋势仍然存在。De Long等人(1990)的开创性金融研究考察了图表分析师和理性投机者的模型。通过明智地利用图表分析师所产生的繁荣-萧条周期,理性的经纪人放大了这些周期,而不是像我们通常预期的那样抑制它们。因此,大幅波动的趋势只取决于图表分析师的影响,而不取决于边际代理人的理性或非理性。
在回顾了上述模型假设的证据,并观察了其中一些关键预测与现实的吻合程度之后,很难想象我们能够忽视图表派和原教旨主义的二分法,而仍然对汇率有透彻的理解。然而,不幸的是,这本书并没有很好地描述这个模型的优点。例如,它没有提供回归期望存在的任何证据,也没有引用De Long等人(1990)的证据来证明模型的普遍性。
然而,即使它的优势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该模型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主导模型,因为它既不符合拥护者的科学严谨性标准,也不符合怀疑者的科学严谨性标准。它违反了追随者的标准,因为它在内部是不一致的。例如,在第六章之前,由于“基本汇率”是随机游走的,原教旨主义者本身是汇率均值回归的唯一来源。基本汇率包含了国际贸易的所有影响——无论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因此,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套利是无效的。然而,作者在第四章中断言,原教旨主义者的预期是基于从商品市场套利中得出的汇率均值回归。
该模型违反了怀疑者的科学严谨标准,因为其宏观经济假设和货币市场微观结构都与现实不符。宏观经济假设商品市场套利是无效的,这与主流模型假设购买力平价持续不变正好相反,但这两种假设都与证据不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购买力平价即使作用微弱,该模型也不再具有稳定的非基本均衡,而且该书的许多分析将不得不重新构建。(尽管如此,正如Frankel和Froot(1986)所表明的那样,大幅波动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该模型的市场微观结构不允许私人信息的作用,因此订单流,即使经验记录显示,订单流对汇率有巨大的影响(Lyons, 2001)。相反,该模型的均衡条件(取自主流模型)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所有投机者都投资于固定供应的债券。这暗示着,债券供应在决定汇率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当外国资产供应在第6章内化时,这一角色变得更加突出。然而,尽管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没有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表明债券供应会影响汇率。债券供应的经验相关性大概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实际上,短期汇率投机者通常使用的是存款或远期合约,而不是债券。
对于模型的表示。要挑战主流模型,一个模型必须激发广泛的热情,而这需要一个符合最高学术标准的论述。不幸的是,这本书并不总是能满足这一愿望。想想这本书对行为金融学的处理。虽然书名承诺了一个“行为金融框架”,但该书的行为基础却很肤浅。行为金融学,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国际经济学家》在引言中只用了两页,在其他地方也只有零星几页。读者不可避免地会被剥夺大量额外的见解和证据,而这些见解和证据中的很大一部分本可以支撑本书的地位。
尤其令人失望的是,发现了一个与行为证据相冲突的重要的行为假设。具体来说,当风险厌恶是内生性时,假设“代理人的风险厌恶随着损失的大小而下降”,这一选择在前景理论中是合理的。但实际上,这只适用于极其巨大的损失。根据“蛇咬效应”——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且现在已经有经验证明(Nofsinger, 2004)——中小规模的损失会带来更多的风险规避。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原教旨主义者是放大还是减弱汇率波动。
这本书在引用选择上也可以达到更高的学术标准。尽管作者从未直接宣称是他们首创了这个模型,但他们很少在文献中引用它的前身或它的近亲。例如,对Frankel和Froot(1986)最初的基本面-技术面汇率模型的引用被推迟到模型的最初阐述之后,并被放到一个脚注中。排除相关文献削弱了模型的案例,因为一些基本面-技术面汇率传统的研究提供了基于回归的证据,补充了书中基于模拟的证据(例如,Westerhoff和Reitz, 2003)。相关文献的排除也使得很难确定这本书的贡献。例如,从文本中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该模型的繁荣-萧条周期的潜力此前是未知的——但这正是Frankel和Froot最初的观点分析。
最后,书中证据的含义有时被夸大了,在一个案例中,证据与模型相冲突,而书中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具体地说,该模型模拟的回报率在一个周期内的自相关系数约为0.2,而在五个周期内的自相关系数仅为0。这与汇率的一个最佳记录特性——短期内缺乏显著的自相关性——相冲突。作者忽略了这种对比:“我们发现,除了一些初始滞后之外,我们的原始回报是不自相关的”(第133页)。
综上所述:在行为金融框架下的汇率中,作者正确地提出了库恩(1970)所定义的汇率经济学正处于一场科学革命之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基本面-技术面汇率模型作为下一个模型,表明它与一些汇率异常现象是一致的,而这些异常现象是主流模型无法解释的。下一个主流模型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The Exchange Rate in a Behavioral Finance Framework, Paul De Grauwe, Marianna Grimaldi.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Exchange Rate in a Behavioral Finance Framework, by Paul De Grauwe and Marianna Grimaldi, looks outside the box for new insights on exchange-rate dynamics. The “box” is the familiar “rational-expectations-efficient-market” paradigm, as the authors refer to the long-standing set of mainstream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most notably the monetary/ portfolio balance model and the intertemporal optimizing model of Obstfeld and Rogoff (1995). The authors examine, instead, a chartist–fundamentalist model based on the Frankel and Froot (1986) original. The model includes only speculators, who forecast in two ways: “chartists” extrapolate past changes and “fundamentalists” always expect a reversion to fundamentals.
The authors are never shy about their motivation: they title their first chapter “The Need for a New Paradigm” and they title their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l “The Broad Outlines of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Mainstream models, they remind us, have little value in predicting exchange-rate dynamics and cannot explain a number of anomalies, including boom–bust cycles in exchange rates, fat tailed returns, volatility clustering, and the apparent disconnect between exchange rates and fundamentals. Their proposed solution is the chartist–fundamentalist model which, as the book shows, can explain all these anomalies.
This review asks two questions. Question 1: Are DeGrauwe and Grimaldi correct that its time to look for a new exchange-rate paradigm? Since many economists would disagree, the review lets Kuhn serve as an impartial judge. His insights suggest the answer is unambiguously: Yes. Question 2: Is the book likely to catalyze its intended paradigm shift? The reviews answer is a qualified: No. There are good scientific reasons to include the chartist–fundamentalist dichotomy in the next paradigm. However, the model itself seems unlikely to be widely accepted because it is internally inconsistent and the rest of its underlying structure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evidence.
Is it time to look for a new exchange-rate paradigm? The most prominent authority on scientific revolutions, Thomas Kuhn, shows that they typically begin with the emergence of anomalies — such as those that have long puzzled exchange-rate economists (Kuhn, 1970). As Kuhn recounts, the conflict between paradigm and evidence lead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to become skeptical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and to challenge the remaining paradigm adherents. The failure of the old paradigm to account for anomalies generates increasing “anxiety” among researchers and a “crisis” ultimately ensues. Paradigm skeptics are not hard to find in exchange- rate economics. Beyond the authors of this book, the lengthy list of researchers critical of the prevailing paradigm includes such luminaries as Kouri, Goodhart, Frankel, Galli, Giovannini, Flood, Rose, Taylor, Evans, and Lyons. To intensify the anxiety in exchange-rate economics, the dominant paradigm has never been blessed with strong supporting evidence, unlike the natural science paradigms discussed by Kuhn (Meese and Rogoff, 1983; Lane, 2001).
According to Kuhn, adherents and skeptics differ in their definition of rigorous scientific inquiry and, in consequence, they often talk past each other. Adherents view any research outside the paradigm as scientifically irresponsible, whereas skeptics are committed to exploring new scientific terrain because they see no point in studying what is, to them, a failed paradigm. These phenomena, too, can be identified within exchange-rate economics today. Todays skeptics in exchange-rate economics typically cite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the dominant exchange-rate paradigm as its critical weakness — but this is the aspect of the paradigm its adherents admire most.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those microfoundations helps that paradigm avoid being ad hoc in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ne that plagued earlier exchange-rate paradigms. Skeptics likewise value internal consistency but consider those microfoundations to be ad hoc in a different dimension: they are at best tenuously connected to reality. In the skeptics view, researchers could analyze infinitely many imaginary worlds, but the challenge of science is to explain the real world. In meeting that challenge there may be little value in a paradigm that is internally consistent yet profoundly inconsistent with reality.
Todays exchange-rate skeptics began detailing their concerns in the 1980s, as evidence accumulated that the dominant paradigms assumptions of continuou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nd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utterly conflict with macroeconomic reality. In the 1990s, the skeptics focus broadened to include the absence of any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ominant paradigms microstructure and the microeconomic reality of currency markets as observed at trading floors, asset management firms, and corporate treasuries. (This concern is illustrated in Goodhart (1988), and Frankel et al. (1996); market reality is described in Rime (2003) and Sager and Taylor (2006).) For example, the dominant paradigm has long assumed that all information is public and the exchange rates reaction to news necessitates no trading, but both these assumptions are now contradicted by substantial evidence from the “new microeconomics of exchange rates” (Lyons, 2001).1
De Grauwe and Grimaldi take issue with a third aspect of the dominant paradigm, its assumption that speculators are perfectly rational. Here, agai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lines up squarely on the side of the skeptics. The assumption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has long conflicted with evidence from psychology (Yates, 1990) and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tself (MacDonald, 2000). As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e assu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513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饮用水微生物群:一个全面的时空研究,以监测巴黎供水系统的水质外文翻译资料
- 步进电机控制和摩擦模型对复杂机械系统精确定位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具有温湿度控制的开式阴极PEM燃料电池性能的提升外文翻译资料
- 警报定时系统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调查驾驶员信任的差异以及根据警报定时对警报的响应外文翻译资料
- 门禁系统的零知识认证解决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车辆废气及室外环境中悬浮微粒中有机磷的含量—-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协议对城市风力涡轮机的无线监控: 支持应用软件和传感器模块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系统在医疗保健中提供位置信息和传感器数据传输的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PLC的模糊控制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外文翻译资料
- 光伏并联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独立应用程序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