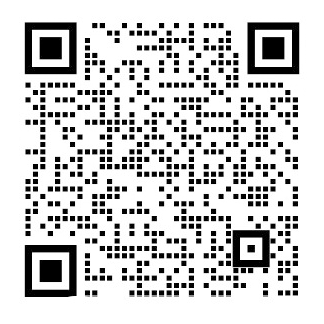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his and her view of housework fairness: A typology of Swedish couples
原文作者 Leah Ruppanner;Eva Bernhardt;Maria Brandeacute;n
单位 University of Melbourne;Stockholms Universitet;Linkouml;pings Universitet
摘要:背景:家务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记录一个公平悖论,即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划分被评估为公平。在像瑞典这样高度平等的国家,家庭和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具有很强的规范性,但并不总是与家庭中同样平等的情况相匹配,而这种状况通常被认为是公平的。目的:利用双方的报告,探讨家务劳动分担与这种划分的公平性之间的关系,以确定瑞典夫妇如何聚集在这些指标中,以及哪些个人特征预测了集群成员。方法:使用2009年年轻成人小组研究浪潮(YAPS,n = 1,026)的夫妻级设计,我们能够在更广泛的夫妻动态中推进研究领域并评估家务经验。我们的方法具有探索性,并使用潜在类分析开发类型学。结果 :我们确定了六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潜在组。模态瑞典夫妇类别包括那些平等分担家务并同意这种安排是公平的(33Scaron;的夫妇)。应用分配正义的观点,我们发现童年社会化,家庭中儿童的存在以及夫妻之间就业,教育,收入和平等主义的分布是集群成员的重要预测因素。结论:我们发现平等分享/公平的伴侣在瑞典语境中最为常见,这表明瑞典广泛的性别政策明显受益。然而,似乎存在代沟,当这种不平等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演时,目睹父母家庭中家务不平等的瑞典妇女越来越不满意。贡献:证明家务分配,冲突和公平可能反映不同类型的夫妇,而不是这些措施的关联。
关键词:冲突;公平;两性平等;家务分工;潜在类分析;瑞典
1.介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务劳动的性别划分一直是广泛研究的焦点。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在瑞典等国家,男性越来越面临着为家务劳动提供更多贡献的压力。然而,家务方面的性别平等尚未实现,即使是在瑞典这样高度平等的国家(伯恩哈特、诺克和林格斯塔德2008;德里比和斯坦福斯2009;埃弗特森和涅尔莫2004;福娃2004;Geist2005)。性别平等,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工作中,在瑞典都是强烈的规范,但并不总是与家庭中同样平等的情况相匹配(伯恩哈特、诺克和林格斯塔德,2008年)。德里布和斯坦福斯(2009)表明,1990年至 2000年间,瑞典男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减少了就业,增加了家务时间,朝着更大的性别平等的方向转变。然而,男性增加的家务劳动不足以缩小家务性别差距,因为瑞典女性即使她们的资源(就业和收入)与男性相同,也会做更多的家务 (Evertsson2014)。事实上,瑞典女性的经济资源只与男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小幅增加相匹配(埃弗特森和Nermo2004,2007)。在某种程度上,家务方面的性别差距反映了个人持有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的差异,更平等的男性在日常家务上花费的时间比更传统的男性更多。然而,即使是在平等主义者中,家务方面的性别差距仍然存在(Evertsson2014)。所以持久是性别不平等的家务,瑞典政府的性别平等 政策指出,“女性和男性必须有相同的责任做家务和有机会给予和接受平等照顾 ”(瑞典政府办公室2016)。对家务劳动中持续存在的性别差距的制度反应是强烈的,影响了政治对话和激励政策(例如,补贴家务劳动外包的RUT立法)。然而,瑞典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家务不公平,以及伴侣(夫妻层面的方法)对不公平的看法影响最大,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现有的文献确定了在瑞典背景下家务不平等和公平之间的复杂关系。诺登马克和尼曼(2003)发现,他们对公平的看法与每个合伙人对家庭、就业和休闲时间的分配有关。女性在家庭中的份额被认为是“公平的”,因为女性工作时间更少(即使是全职工作),因此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做家务。然而,时间趋势数据显示,瑞典男性,而不是瑞典女性,增加了自由支配时间(休闲和睡眠),而(与1990年和2000年相比)(德里比和斯坦福斯2009年)。正如这些数据趋势所显示的那样,瑞典女性为了获得更多的家庭时间而牺牲了休闲时间,尽管她们花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更低。尽管存在这种差距,但很少有女性认为这些分配不公平。瑞典夫妇很少平等地分担家务,但只有30%的妻子和20%的丈夫认为这是“不公平的”(Ahrne和Roman1997)。显然,家务悖论——不平等的家务分工——即使在高度平等的瑞典背景下仍然存在。即使根据这项研究,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采用夫妻层面的方法来调查伴侣的家务劳动公平报告是否一致。这种区别很重要,因为家务劳动不平等是关系破裂的一个预测因素(弗里斯科和威廉姆斯, 2003年;奥拉和加勒,2014年;鲁帕纳、布兰登和图鲁宁,2017年)。
我们通过评估这些关系如何映射到瑞典女性的生活经历来解决这些差距。现有的关于家务和公平的研究狭隘地集中在个人层面的报告上(登普西1999年;克鲁沃、海辛和范德弗列特1997年;珍珠、巴克斯特和泰2015年)。然而,合伙人之间的家庭劳动谈判是非常活跃的。由于缺乏关于这些措施的夫妇级数据,因此禁止进行直接勘探,这是该领域的一个主要限制。事实上,Smith和他的同事(1998)主张“将问题(家务不平等和平等)重新概念化为夫妻或婚姻的属性 ”(p。325).我们的研究方法是探索性的,开发一个类型学使用潜在的类分析,但很重要的是,鉴于很少知道之前的发现从瑞典数据(持久的性别不平等和公平的看法)捕捉所有瑞典夫妇的经验或只有某些类型的瑞典夫妇(啊和罗马1997;诺登马克和尼曼2003)。
人们的期望是,工作和家庭特征的变化构成了夫妻对家务和公平的看法。许多瑞典女性采用一种“组合策略”,其特征是在产假后兼职工作,以保持对劳动力市场的依恋,同时也花时间与学龄前儿童在一起(伯恩哈特,1988年)。尽管大多数瑞典女性报告平等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以母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存在:有小孩的妇女通常工作少于全职,大多数人将工作时间减少为“长兼职”,即每周 2034小时(伯恩哈茨2014)。这些性别差异也反映在使用家庭-响应政策。自1978年以来,父母有合法权利将工作时间(相应减少工资)减少到 75%,直到孩子达到8岁。这一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性别划分,但母亲们比男性更频繁地利用这一权利(拉尔森,2012年)。这意味着许多母亲兼职工作时间很长( 30小时以上),这是瑞典人不同的特点。女性的兼职工作与更多的家务劳动相结合,这可能被认为是公平,也可能不公平(Evertsson2014)。现有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会认为他们的家务分配是公平的(Ahrne和Roman,1997年;诺登马克和尼曼,2003年)。尽管有这种公平的看法,但文化仍然紧张,年轻的瑞典夫妇赞成平等分工,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将这一理想应用于现实(伯恩哈特、诺克和林格斯塔德2008年)。离婚在不公平分担家务的年轻瑞典夫妇中更为常见,这表明家务讨价还价中的紧张关系有害(Olah和Gahler2014)。由于这些原因,需要了解一系列理论动机的措施中的集群成员关系是必要的。
我们通过应用来自青少年小组研究(YAPS;n=1,026)的夫妇水平的数据来解决这些限制。青年小组研究(YAPS)是准备做出贡献的独特准备。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家务分担和这一部门的感知公平之间的关系——使用双方的报告——以确定瑞典夫妇如何在这些措施中聚类,以及哪些个体特征预测集群成员。我们权衡了三个重要的问题:1)瑞典夫妇是否聚集在家务分配和公平报告上?2)家务公平的差异如何影响群体成员?3)的工作特征和家庭特征解释了这些集群中的成员身份,以及它们是否因性别而异?夫妻水平数据的应用解决了Smith和同事(1998)的呼吁,在更广泛的夫妇动态中评估家务经历,并为被视为公平的家务不平等的矛盾关系是否抓住了规范的瑞典人的经验提供了见解。我们的两步建模方法,首先识别跨家务部门和双方的公平报告的潜在集群,第二步识别与群体成员相关的个人特征,提供了对瑞典夫妇认为家务最有争议的更深入的理解。这种模式有助于确定有关系破裂风险的夫妇的特征,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解决方案,以纠正家庭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Olah和Gahler,2014年)。
2.类型:瑞典语的案例
我们希望我们对瑞典夫妇的类型将被分为三个维度:家务不平等、对公平的看法,以及夫妻对家务公平的同意。为了评估这些关系,我们利用YAPS的夫妻级设计来包括公平报告中的不一致性,预计这对于那些家务分配不平等的人来说是最严重的。我们大量利用现有的家务公平理论来解释我们的类型学,并假设哪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将解释群体成员身份。我们轮流做。
2.1解释家务劳动的公平:分配正义的方法
瑞典妇女的公平程度很高,即使家务传统上是分开的(Ahrne和Roman,1997;诺登马克和尼曼,2003年)。分配正义理论被用来解释这个悖论,它分为三个维度:结果、比较参考和理由(汤普森1991)。“结果”捕捉了夫妻客观的家务分工。简单地说,一个公平的家务分工被评价为比不公平的分工更公平。“比较参照者”是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即个人将通过比较其家务贡献与他人的贡献来决定其家务分工的公平性。其他人的家务贡献可以作为自己评估家务公平性的基准。在我们的案例中,我们估计了儿童社会化对集群成员身份的影响。具体来说,我们测试了代际比较,特别是在一个有传统家务部门的家庭中成长,是否可以解释集群成员关系。分配正义理论预测,受访者在家里进行传统家务分配(他们的母亲比父亲做的更多)更有可能证明当前的传统家务部门(女性伴侣做得更多)是公平的。最后,“理由”反映了家务劳动部门的意识形态验证。具有平等主义性别角色期望的受访者更有可能认为不平等的家务是不公平的,而在传统的受访者中,不平等的划分争议较少。我们将我们的估计扩展到性别角色意识形态之外,包括就业状况。正如以往的文献记载,全职工作是认为传统家务分配是公平的 “理由”(诺登曼和尼曼2003年)。我们希望那些有兼职工作伙伴的人会报告不平等的家务部门是“公平的”。我们还通过扩大对妇女资源的措施,包括相对收入和教育来扩大理由。我们希望收入与伴侣相同或以上的女性对不平等的家务安排不太满意。此外,我们预计女性将会有更高的水平教育不太可能证明家务劳动的不平等分工是公平的。因此,我们期望比性别角色意识形态更全面的女性资源,来解释我们的集群。
分配正义的观点得到了跨国的支持,因为家务劳动的分配和性别角色的期望被证明构成了不公平的感知(巴克斯特2000;珍珠、百特和泰2015;鲁潘纳2010)。然而,这些矛盾的发现——被认为不公平的家务是公平的——需要额外的调查。具体来说,问题仍然存在:这些关系是由单一经历驱动的,还是反映了更广泛的个体特征分组?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确定了争论的类型,特别关注女性和男性对家务不平等的看法,以及夫妇的不公平报告的不一致。
2.2连接公平来解释瑞典的类型
我们希望家务劳动的分配和夫妻的公平报告能形成四种广泛的类型。我们从家务劳动方面的平等开始,因为理论预测,对公平的感知与客观的家务劳动部门有关(汤普森,1991年)。从瑞典性别平等政策的明确目标来看,我们预计最大的群体将包括平等分担家务并同意这种公平分配(“公平/同意公平”的夫妇)。大量先前的研究表明了家务平等在瑞典的重要性(Ahrne和罗马1997;埃弗森 2006,2014;埃弗森和涅尔莫2004,2007;福娃2004;Geist2005;钩2006;鲁普纳2010)。因此,我们期望那些实现家务平等的人也报告公平,与夫妻内部的一致性。如果瑞典的性别平等主义真正被大多数瑞典夫妇所内化,那么这个公平/公平的群体应该是模态类别,我们期望个人持有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理由)和家务社会化(比较参照)对群体成员的预测较少。相反,我们期望对家务劳动的公平划分是瑞典的一种规范经验,而不是由平等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所驱动。
第二类包括那些或多或少平等地分担家务的人,但妻子仍然做得更多,因此认为这种划分不公平,而丈夫则不公平(“半公平/争议”——她报告不公平,但他报告公平)。应用分配正义理论,我们预计这种集群在全职工作和拥有更平等主义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的人群中最为常见。接下来是那些有传统家务安排的人,女性承担的份额更大。此分配应该会产生两个集群。一方面,这种不平等可能受到高度争议,这反映在妇女的不公平报告上(她说这对她不公平)。根据分配正义的观点,这些瑞典群体应集中在那些持有平等主义性别角色期望的妇女和那些全职工作的妇女之间。男性是否认为这种传统的安排是“公平的”,也应该取决于男性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平等主义的男性认为不公平,但传统的男性认为这些分配更公平。这些群体还可以捕捉到那些通过传统家务分配长大的人,将他们的家务分配与父母进行比较,并验证它是公平的。另一方面,双方可能都认为这些不平等的家务分工是公平的(“传统/同意公平”)。在这里,我们再次期望性别角色意识形态和儿童家务劳动社会化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具体来说,我们希望那些有传统性别角色期望和传统儿童家务分配的人能聚集在这一群体中。
第三类是女性做更多的家务,夫妻双方都认为这种划分对她不公平。在这些夫妇中,对家务的看法被准确地判断,在夫妻中始终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分配正义的观点预测,这些夫妇在其性别角色的态度上将更加平等。相对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和那些有全职工作的女性也最有可能认为不公平的家务劳动部门是不公平的。在最后一组调查中,我们有一对“打破常规”的瑞典夫妇。在这对夫妇中,男人做了大部分的家务。由于这是一种新兴的家庭形式,在其他地理环境中不太常见,因此对这些夫妇缺乏理论解释,而且由于这种安排的性别维度而更加复杂。一方面,分配正义的观点,即性别中立的,预测不平等的家务分配将导致对双方的不公平的看法(“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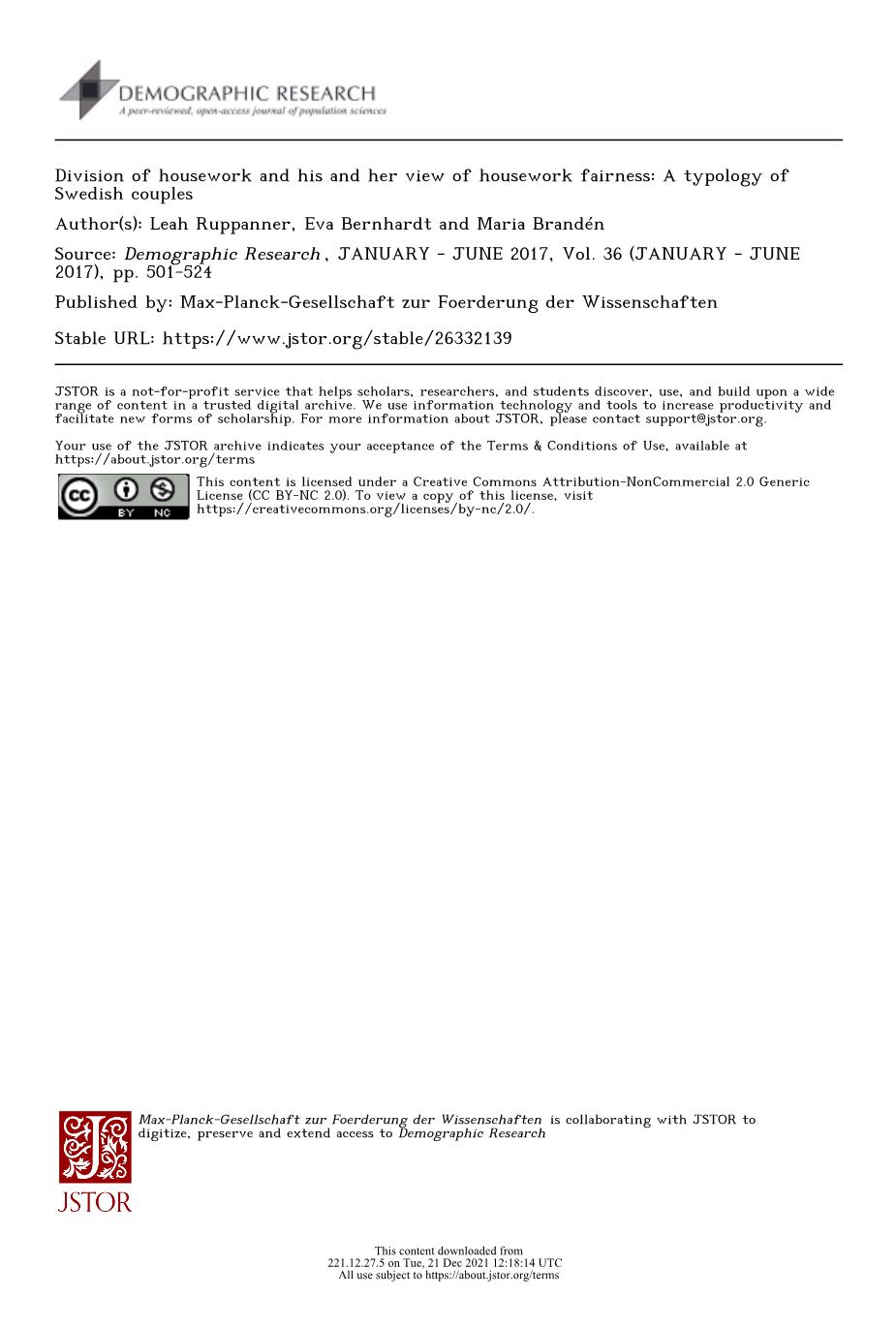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689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饮用水微生物群:一个全面的时空研究,以监测巴黎供水系统的水质外文翻译资料
- 步进电机控制和摩擦模型对复杂机械系统精确定位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具有温湿度控制的开式阴极PEM燃料电池性能的提升外文翻译资料
- 警报定时系统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调查驾驶员信任的差异以及根据警报定时对警报的响应外文翻译资料
- 门禁系统的零知识认证解决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车辆废气及室外环境中悬浮微粒中有机磷的含量—-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协议对城市风力涡轮机的无线监控: 支持应用软件和传感器模块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系统在医疗保健中提供位置信息和传感器数据传输的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PLC的模糊控制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外文翻译资料
- 光伏并联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独立应用程序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