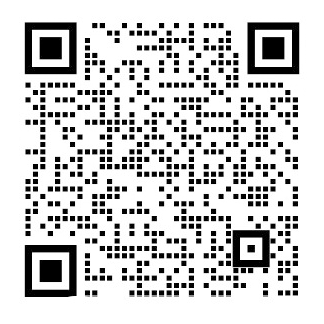中国幼儿园师生母子合作写作:元语言意识、母体调解与识字习得
原文作者:林,丹1张麦克布莱德,凯瑟琳2阿兰姆莱文,IrIS3
作者单位:1香港香港教育学院2中国香港大学,香港3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发表杂志:阅读研究杂志。2011年11月,第34卷第4期,第426-442页。4张图表。
摘要:本研究考察了香港63名中国幼儿园教师的文字阅读和写作对母亲写作的中介作用以及一些元语言和认知技能的关系。整个母亲的写作调解过程被录了下来,其中母亲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孩子写出12个两个字符的单词。本研究复制并扩展了先前关于母亲帮助孩子写汉字的认知策略的研究。母亲的典型中介策略与孩子的独立阅读和写作呈显著正相关。此外,母体写作中介与汉语单词阅读,但不与单词写作,甚至与元语言和认知技能,包括语音意识,形态意识,字形加工和视觉知识,统计上受控。研究结果强调了母亲早期搭建脚手架对促进儿童识字能力的重要性。
关键词:单词;角色;语义根;语音根;结构
本研究主要关注了香港Chinese儿童早期识字技能的母子共写,包括单词阅读和单词书写。这在香港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孩子早在3.5岁就开始在学校学习正式的阅读和写作(香港教育部,1996)。这种非常注重识字的实际现实至少部分归因于香港政府高度重视双语或三语识字和语言水平的事实。事实上,香港是如此独特,开始这种正式的指示,这样早(张扬,NG,2003)。李和拉奥(2000)对160名香港的中国父母进行了调查,发现超过70%的人教2到6岁的孩子读汉字,超过50%的父母说他们在家里教写作。此外,这些父母中的大多数(约60%)。R英国扫盲协会2010年。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地址:9600 Garsington Road,Oxford Ox4 2dq,UK and 350 Main Street,Malden,MA 02148,USA认为学前教育是开始读写教学的适当时机。正如先前的研究表明,母亲在家庭识字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Chaoamp;Tseng,2002;Ho,1996;Meisels,1998),在本研究中,我们只关注母亲与子女的互动。从广义上讲,我们研究了母子共同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儿童自身独立单词阅读和写作的独特差异,特别是与先前确立的阅读相关的认知和元语言技能有关的差异。
母子联合写作(Aram,2007年;Aramamp;Levin,2001年、2004年;Burnsamp;Casbergue,1992年)已被证明与跨文化儿童的识字能力发展有适度或强烈的关联。母子联合写作背后的理念是,孩子们在母亲等有技能的伙伴的支持下,学习在给定的任务中表现得更好,比如复杂的单词写作任务,遵循Vygotsky(1978)提出的“近端发展区”的理念。例如,Aram和Levin(2001年)发现,在希伯来幼儿中,母亲调解与单词阅读和书写技能以及语音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进一步对这些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即使2.5年后,母亲的调解仍然可以预测孩子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一项针对中国幼儿的研究(Tan,Spinks,Eden,Perfettiamp;Siok,2005)也表明,写作技能极大地促进了阅读能力,尽管这项研究只关注儿童自身的写作技能,而不是共同的母子写作。
在过去的工作与香港华人儿童,林等。(2009)通过对67名香港母子二人写作的观察,共抽取六篇认知分享策略。这些研究者随后建立了一个有序的文献中介量表,包括从低到高水平的复制、笔画、视觉化、分割、语音功能和语素六个独立的策略,基于它们与儿童独立阅读技能的相关系数。这项研究(Lin等人,2009年)研究了三个级别的幼儿园儿童的所有这些策略,即第一年(3-4岁)、第二年(4-5岁)和第三年(5-6岁)幼儿园。较低层次的调解集中在让孩子复制汉字或在书写中纠正孩子的个别笔画形状等策略上。更高层次的中介更侧重于意义相关(即形态)知识,例如指出两个词如何共享同一个字符(或语素),或指出两个字符共享同一语义根式(大多数汉字的基本意义单位),表明语素的广泛类别。例如,在不同的角色中,母亲可能会指出,两个角色具有相同的部首,这表明与嘴巴有关(例如,表示亲吻、唱歌和吃饭的角色都包含“嘴巴”部首)。(参见图2了解更多语义部首示例。)研究结果表明,母子二人组在年龄较大的儿童(4至6岁)中使用了更先进的策略。然而,即使控制儿童的年级水平和母亲的教育水平,更先进的策略也与儿童的独立单词阅读有着独特的联系,这表明儿童单词阅读的个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到母亲在儿童早期写作中的脚手架做法的影响。
在那项研究和目前的研究中观察到的策略是公认的独立或分类的。许多被认为是低水平的策略,例如让孩子简单地复制母亲打印的单词,在所有年龄段的孩子身上重复出现。然而,与此同时,这项研究(Lin等人,2009年)和之前关于字母正字法的研究(如Aramamp;Levin,2001、2004年)也验证了我们在本研究中采用的策略顺序,从简单到更具意义。这样的排序最终使我们能够计算出一个分数,即母亲在写作练习中使用的典型的母亲调解水平。这个单一的分数最终可以被检查与儿童的独立元语言技能和单词读写自己。
因此,本研究扩展了Lin等人的研究。(2009)为了复制和完善规模。此外,虽然之前的研究只检查了儿童单词阅读的量表,但目前的研究将其扩展到了儿童的早期写作技能。重要的是,我们还包括了许多元语言能力,这些能力在以前的研究中被证明与早期汉语识字能力的发展有关,试图将这些认知技能与母子互动区分开来。本研究采用的该量表的水平如图1所示。图2展示了一个汉语单词的一些特征,包括每个字符中的语音和语义根式,以及这些特征是如何在一个给定的字符中构成的,并在新修订的尺度中进行了扩展。
尺度的细化首先集中于在中间层(第4层)中添加“指出角色结构”的策略。这一层次的重点是正字法信息,即如何使用语音和语义部首在位置上表示字符。在以往的作品中,人物内部结构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如舒安德森,1997;舒陈安德森,吴轩,2003)。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将重点放在母亲如何明确地关注她们联合写作活动中单词中的字符结构上。例如,在单词(花瓶)中写(花)时,母亲可能会向孩子指出(花)是一个具有组件的上下结构。
图1文雅调解量表。
图2。汉语单词分解的例子。
在顶部和底部。这意味着语义词根在顶部,语音词根在底部。因为这个重点是利用汉字中的成分知识(通常是单个汉字的语音和语义部首),所以我们将这一层次定为高于成分中介,但低于部首中的语音(即语音)或语义(即语义)的显式重点。这一决定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后者注重声音和意义,代表了对汉字中书写成分功能的更深入的理解。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先前工作(Lin等人,2009年)中证明的最高水平的母体调解扩大到了本研究中的两个水平。下一级(即6级)是语义根级,即字符内级。例如,在编写字符时
(蜜蜂),一位母亲可以解释它是一种昆虫,它的文字包含了它左边的语义根(昆虫)。
本研究所用量表的最高水平(第7级)为整体人格水平。在这个层次上,是对目标字符和其他字符或同一字符(换句话说)的解释或比较。例如,在写单词(luggage)中的字符时,母亲可能会告诉孩子这个字符与您的姓氏相同(意思是两个字符都写为“lee”,并发出“lee”)。我们将其概念化为当前研究中的最高水平,因为它要求使用儿童对单个角色的先验知识。
在学习汉语写作的最初几年里,“练习与实践”的传统哲学在汉字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吴、李、安德森,1999)。Lin等人例如(2009年),发现76%的母亲调解的中文单词写作包括幼儿园的复制策略,这种复制策略与儿童的实际单词阅读负相关。
然而,我们的目标是在本研究中突出其他可能更有效地获取汉语识字的策略。此外,从概念上讲,复制策略本身可能反映的更多是书面形式的自主授权,而不是从先前工作的观察中得出的特定认知中介成分(例如Lin等人,2009年)。其他地方讨论的书面调解的其他方面(例如,Aramamp;Levin,2001;Lin等人,2009)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自主授权策略。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排除了在本研究中非常普遍的复制策略,只关注母亲用来帮助孩子学习写作的其他认知策略。因此,我们使用的比例,从以前的工作中提炼(Lin等人,2009年),如图1所示。
除上述改进外,文盲调解量表中包含的其他策略与Lin等人相同。(2009)成立。原则上,已制定的序贯性母亲调解量表基本上与何、陈、李、曾和阮(2004)的工作一致,表明儿童的阅读习得至少跨越了三个广泛的阶段。这些策略的范围从死记硬背的新字符到逐步获得位置和功能规律的汉字。最终,孩子们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跨字符或词级特征上。Ho、Yau和Au(2003年)关于儿童写作发展的研究也记录了类似的观点。
除了在联合写作活动中进行母子调解(至少可以部分视为家庭环境的一个方面),一些研究还证明了认知和元语言技能对中国儿童早期识字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语音意识(例如Hoamp;Bryant,1997;McBride Changamp;Ho,2000;Siokamp;Fletcher,2001)、形态意识(例如McBride Chang、Shu、Zhou、Watamp;Wagner,2003)、正字法意识(例如Li、Pengamp;Shu,2006;Shuamp;Anderson,1998)和视觉技能(例如Hoamp;Bryant,1999;Huangamp;Hanley,1994)。所有这些都与以前工作中中国儿童的单词阅读有关。其中一些问题也与文字写作有关(例如,Tong、McBride Chang、Shuamp;Wong,2009年),但很少。
综上所述,本研究考察了香港中国幼儿园教师的文字阅读和文字写作与母亲写作中介的关系,以及一些与年轻中国儿童识字能力相关的元语言和认知技能。此外,由于非语言智商和母亲的教育水平也被发现与以前一些工作中的早期识字技能有关(例如,Aramamp;Levin,2001;Lin等人,2009),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本研究。母亲调解写作策略是本研究最感兴趣的,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至少对中国家庭来说是如此。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和完善了以前使用的母婴联合写作量表(Lin等人,2009年),然后重点关注其与早期识字技能各方面的独特联系。
方法
参与者
参加者为63对母亲和他们的孩子参加第三年的幼儿园在香港。女生30人,男生33人,平均年龄5.81岁(5.16-6.41岁,SD5.29)。
所有的孩子和母亲都是讲粤语的本地人。在香港,孩子们早在幼儿园的第一年就开始正式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幼儿园在香港的最后三年[K1,K2和K3]),当他们大约3.5岁的时候。香港幼儿园的教学,实际上是所有的交流,都是在香港的广东话(香港教育部,1996)进行的。根据家长的报告,所有参与的孩子在学校和家里都有阅读和写作的经验。
措施
母子联合写作中的母亲调解任务。母亲与子女共同参与联合写作活动的录像带是衡量母亲调解质量的基础。图片卡上描绘的12个两个字符的单词(6对,如附录A所示)以随机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呈现给母亲-孩子二人组,母亲们被要求帮助他们的孩子写“他们认为合适”。为了避免让孩子直接复制书面文字,并确保母亲有尽可能多的自由与孩子一起安排写作工作,我们使用了图画卡片而不是印刷文字来表示要写的文字。为了确保母亲和孩子们正在写下他们想要写的单词,当实验人员把每个单词放在一张图片卡上时,他们都会说出来。在整个过程中,母亲和孩子们都用他们的母语,也就是广东话。
这些选定的12个单词分为五类,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不同的写作促进策略,如Lin等人(2009)在他们的研究中。请注意,这些单词是随机出现的,母亲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单词之间应该或确实有任何共性。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母亲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可能向孩子指出的这些单词(或孩子可能已经学会的其他单词)的模式。
我们对单词的配对让他们有机会强调一些涉及声音、意义、结构等的模式。如附录A所示,单词之间的五类共性之一是同音词。例如,在单词的配对词(孔雀-恐龙)中,单词中带下划线的两个字符是同音词。因此,母亲们本可以指出,尽管这些字符的书写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发音相同。第二类是同形词。例如,在单词对(luggage-bank)中,单词中带下划线的字符写得相同,但有不同的含义和发音(类似于“鞠躬”,如“鞠躬给观众”和“头发上有一个漂亮的鞠躬”)。第三类是逆序字符。例如,在单词对(蜜蜂-蜂蜜)中,单词中的两个字符是相同的。但是,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的顺序是相反的。我们认为第四类涉及视觉上相似的字符。例如,在
(自由-兔子),下划线字符有相似的外观,但字符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和发音。最后一类涉及到语音成分相同但语义成分不同的词对。例如,在这对(男性)中,单词中带下划线的字符具有相同的语音成分,但语义成分不同。
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水平以7分制衡量,1分为三年级或以下,2分为4-6年级,3分为7-11年级,4分为12-13年级(高中最后两个年级),5分为一些学院,6分为大学毕业生,7分为研究生培训。
非言语推理。Raven标准渐进矩阵(RCPM;Raven,Courtamp;Raven,1995)中的集合A和B被用作儿童非言语推理的估计。共有24项,因此,这项任务的最高可能得分是24分。
视觉空间关系。视觉空间关系任务(Gardner,1996)评估儿童的空间定向。它包括16个项目,每个项目由5个数字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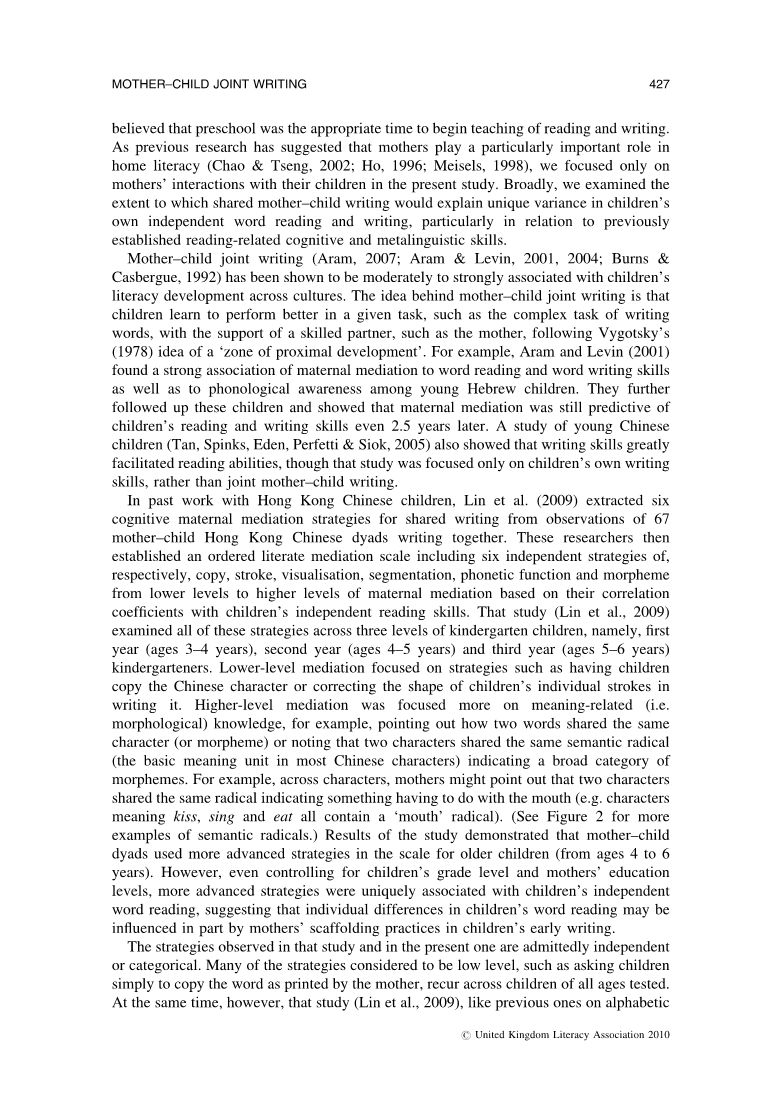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839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饮用水微生物群:一个全面的时空研究,以监测巴黎供水系统的水质外文翻译资料
- 步进电机控制和摩擦模型对复杂机械系统精确定位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 具有温湿度控制的开式阴极PEM燃料电池性能的提升外文翻译资料
- 警报定时系统对驾驶员行为的影响:调查驾驶员信任的差异以及根据警报定时对警报的响应外文翻译资料
- 门禁系统的零知识认证解决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车辆废气及室外环境中悬浮微粒中有机磷的含量—-个案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协议对城市风力涡轮机的无线监控: 支持应用软件和传感器模块外文翻译资料
- ZigBee系统在医疗保健中提供位置信息和传感器数据传输的方案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PLC的模糊控制器在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应用外文翻译资料
- 光伏并联最大功率点跟踪系统独立应用程序外文翻译资料